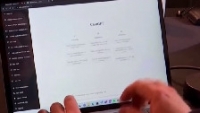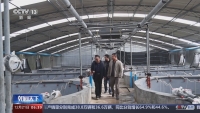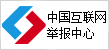正文
專訪濟南畫院院長、濟南市美術館館長吳建軍 一個畫人的水墨自傳

吳建軍
筆名:無山,1962年生于山東萊蕪。1985年畢業于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工藝繪畫系。現任濟南畫院院長、濟南市美術館館長,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山東省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山東省中國畫學會副秘書長,山東文人書畫院副院長,山東致公書畫院副院長,濟南市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致公黨濟南市委員會常委、文化藝術委員會主任,濟南市政協常委。

《城》 2012年 180x150cm 水墨紙本

《故園》 2014年 180x150cm 水墨紙本

《城》 2012年 150x180cm 水墨紙本

《城》 2012年 150x180cm 水墨紙本
專訪濟南畫院院長、濟南市 美術館館長吳建軍——
一個畫人的 水墨自傳
本刊記者 張海平 張霞
許梅 攝影
作為畫家,吳建軍是得陳履生、呂品田、鄧福星、單應桂等國內、業內著名評論家、前輩畫家贊賞的水墨行家。身兼濟南畫院院長、濟南市美術館館長等職務,吳建軍又擔綱一部分藝術公共責任。當下環境中,我們傳達水墨是為了傳達什么?水墨以及美術館在娛樂、綜藝、消費占據主導的當代生活中又獨具什么精神意義?吳建軍的水墨之路是如何開啟?吳建軍對水墨有什么獨到的見解?針對以上種種話題,本刊記者近期采訪了吳建軍院長。
現代美術館里的
“畫魂穿越”
一張辦公桌,兩條黑皮沙發,墻上幾幅丹青,文茶具隨意擺放,采訪安排在吳建軍的辦公室。斯是陋室,卻也窗明幾凈,隔絕此刻正喧鬧堵塞著的城區街道,屋中沉靜質樸仿佛能聽見秋葉掉落的聲音。
“你們看看墻上這幅作品。”一面泡茶,吳建軍一面指著墻上一幅頗具“現代精神”的小畫對記者一行笑語。
幾張手指指骨的X光片隨意組合于宣紙之上,黑色的底片上呈現出細小的白色幼童手骨,頗具視覺張力,宣紙下側署字《石頭》。
倒是有幾分意味,是寓意人的骨頭才是最堅硬的精神物質,哪怕幼童手骨?
“這是您最新的創作嗎?”記者邊想邊問。
“這是我2歲外孫的大作。”吳建軍一句話逗得記者不由發笑,氣氛瞬間輕松下來。
“我常想藝術是什么啊?比如杜尚的《小便池》,一個幼童是否也能有此創意?藝術是反叛?是赤子之心?是歸真?為什么小孩做一幅涂鴉不能稱其為藝術?”
身著黑西裝白襯衫的吳建軍仿佛如他的黑白水墨一樣簡單透徹,頗具性情。記者尚未發問,吳建軍已然小胡子一撅,開始進行自我對話。從達利、畢加索到八大山人、明代文人畫,古今中外,畫藝、畫心,吳建軍自行游走于另外一個自我的私密空間。
順著吳建軍的思緒,記者一行回到了他的青少年時代。
論起吳建軍的水墨道統,他認為那是一種冥冥中的畫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出生于小城萊蕪,接觸繪畫純屬天性中的敏感。他的童年記憶正逢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化產品單調的年代紅寶書成為家家戶戶的必備讀物,與眾人相反,幼年的他對那些抑揚頓挫的口號毫無興趣,反而被紅寶書鮮艷的色彩及上面的毛澤東頭像吸引。
對顏色、結構、視覺沖突的敏感和天賦在那個時期便被激發,七八歲大小他便開始比照這紅寶書上的偉人頭像描摹“創造”起來。及至小學繪畫課上,他的美術興趣徹底被激發出來,成為學校黑板報設計加繪圖的多才學生,這種板報情結一直延續到他的青年時代。
1981年吳建軍歷經兩次高考,終以泰安考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工藝繪畫系。至今猶自豪地回憶起京劇大師方榮祥來校講座以及新任院長張一民到任學術講座的海報和招貼皆由自己操刀制作設計。除此之外,吳建軍還同如今的工藝美院院長、當年的同學潘魯生一起負責完成《工藝美術學刊》創刊號發行的設計和手繪工作。
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吳建軍無比懷念大學時代給予自己的飛速成長。彼時剛剛結束十年文革,人人似如饑似渴地海綿一般瘋狂吸收著學問知識,美術新潮、傳統技藝、西方思想紛紛涌入視野。學生隨時可以拜會畫壇名聲鼎盛的老先生,同學結伙搭伴逃票到北京只為看一場中國美術館里的展出,有幸聆聽吳冠中、黃永玉等老一輩藝術家的授課。寫生是他良好的習慣,1983年初冬時節,學生時代的他畫情突起,背著畫夾清晨跑到工藝美院后山千佛山腳下寫生忘記時間,恰逢出來散步的楊耀老師撞見才被招回,那時他的手指已經麻木,腿腳凍得僵直,耳朵也已生了凍瘡……辦公室一片寧靜,只余吳建軍激情的講述。講到興處,他即興來上一段《智取威虎山》山東快書選段,記者一行亦仿佛回到那個激情的年代,隨著吳建軍的畫魂在時空里穿梭、跋涉、游蕩。
幾多歲月礪練了吳建軍那些精工于“符號作用”的繪畫語言,積累了比較豐厚的傳統筆墨技巧。幾年后隨著視野的拓展和審美領域的多元,他開始認識到工藝美術時期使用的藝術語言比較嚴格鐵定,但也正是這段“工藝美術”的經歷造就了他扎實的造型能力和筆墨技法。
“建軍的畫里西方元素更多,他畢竟學過設計,畫面構成包括黑白灰的結構關系都有。”同行梁文博曾這么評價。著名評論家陳履生先生說,吳建軍“探索意向是多元的”,很大程度上這正得力于他工藝美術出身。
“那個年代學生窮,干過很多調皮事,比如畫公交月票以假亂真,閑暇時去幫各大商戶店鋪寫寫畫畫賺點學費,這些實踐經驗一定程度上練就了扎實的手上功夫。”吳建軍笑著回憶。
無需為山河立傳, 只需在山河里相遇自我
講述正在興頭,美術館攝影工作室的劉書彤抱著一摞剛剛托裱好的吳建軍的畫卷推門而入。記者一行圍坐一起欣賞起來。
一幅名為《長空》的作品跳入記者眼睛。名為長空實則不見長空,只見一派生機,這幅作品色彩運用激情大膽,從山巒到云彩到高空之間空靈剔透,精彩鮮亮跳蕩自然之感。仿佛試圖把虛實相生的手段運用到色彩處理上,云靄中間的柔粉過渡到巒頂的淡青,再有山體的墨黑,長空浩蕩中間的留白,給人氣象萬千真氣彌漫之感,別有雅致素淡的美。
另外一幅《冷月》畫風截然相反,月光如水,撫摸著山川河流、蒼林翠柏;冷月高懸,天地間充盈著一片孤寂靜逸之氣;不見冷月,只見濃濃相宜的墨色,引頸長嘯的駿馬。吳建軍的畫風在這里突然變成了留白頗多、若隱若現的淡墨。
至于《月下林更幽》、《道》等則又以大塊潑墨為主,整個畫面幾乎全是黑暗,畫面主體是濃重的山影和密集的樹林,烏云遮月般徐徐而來的山巒,若明若暗、若清若濁的月光與陽光,冰河一般緩緩游動的薄云濃霧,無不籠罩在某種濃得化不開的激情幻想、如泣如訴的氛圍之中。
“為什么畫風這么多的差異?”記者詢問道。
“濃也好淡也好,最重要的是筆墨造境,突破、發現、尋找自己。”吳建軍向記者詳細介紹起了幾幅作品的創作時期及自己對筆墨的各個階段的認知。
藝術的道路從來不是一條平坦之路,從工藝美院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再次經歷一個輪回。“忘而再現。”吳建軍這么向記者總結。
1990年3月吳建軍前往北京畫院進修,這個階段他開始了自己繪畫從“物象”到“意象”的變遷,如何尋找藝術本體之外的“境界”,如何“造境”成為他苦苦思索的問題。
如同所有丹青妙手一般,游走山河感受著山川的挺拔壯美,水的嫵媚潤澤,體驗生活的艱辛和人生的冷暖,成為吳建軍這個時期的重心。從黃山到華山到九寨溝,凡有閑暇他便將身心沁潤于自然造化的名山大川中間,耽迷忘往,如癡如醉,饑時扒花生,生吃玉米,渴時飲山泉,喝河水,一本本厚厚的速寫本堆滿床頭。
“寫生是重要的手段,繪畫首先確需胸中有丘壑。”見到風景便即刻速寫的習慣至今仍被吳建軍保留下來,記者在他辦公室隨手翻開一本速寫本,從遙遠的印度、巴基斯坦到濟南南部山區,他幾乎走到哪里筆頭勾勒到哪里。
“經常一畫起來就癡了,兩三個小時停不下來。有次陪家人朋友去南部山區游玩,停車的功夫突然看到一片好景,就自個留在車里畫了起來。恰好有朋友經過認出我的車,還以為我在密謀什么壞事兒呢。”他談起自己的糗事發出爽朗笑聲。
游歷山河只是其中一個階段,畫山其實是畫心,畫山還要遠離山。山川里的寂寞行走帶給他內心的寂寞,將山水放遠,將心中的寂寞寧靜拉近才真正帶給了他突飛猛進。
繁瑣的工作之余,書齋面壁;閑暇和前輩藝術大師們靈魂相逢,聆聽他們的諄諄教誨。歷經十數年吳建軍終于造出自己內心的境,尋找到自己的“情”。
“山河乃自然造化,我們沒有能力為其做傳,只能為我們自己的內心做傳,只能在山河中遇見真正的自我,發現自己心靈里的自然。”吳建軍總結道。
如同吳冠中從銀灰時代到黑色時代的變法,如同林風眠“融合中西”的藝術開拓,繪畫要不停嘗試。1994年之后吳建軍一次次改變、突破著自己的筆法,從淡墨到潑墨無不探索。
心靈感悟、哲學參悟提升著他的藝術表現力,終于形成了自己的筆墨特點:無論用筆側鋒疾行,粗獷剛健,還是淡柔之濕筆相輔,層層渲染,求圓融渾厚之勢。他總能尋到自己內心的幽深曲折、寧靜淡遠,自己筆下的濃淡相宜,景情相溶,現實與幻想交替。
一場關于大水墨的
“中西對話”
不覺之間已由清晨聊至正午,吳建軍結束自己丹青生涯的對話,帶領記者一行參觀起濟南市美術館。
除了畫家的身份,濟南畫院院長、濟南市美術館館長的職務,更賦予他另外一重責任:推廣公共藝術、文化惠民、帶動濟南文化氛圍。
濟南市美術館建筑面積為1.5萬余平米,由法國著名AS公司場館設計,共八個展廳,棱角多面切割狀的外墻與國際接軌的設備,使其猶如一顆鉆石一樣璀璨、神秘。如何利用好這么先進的市政惠民工程,成為身為館長的他的另外一個工作重心。
吳建軍帶領記者參觀了一樓展廳楊勁松的綜合材料繪畫作品和二樓、三樓的國際版畫展出作品。
“像楊勁松的作品新銳大膽,整個畫展還是中國水墨的表達卻采取了各種牛仔褲、麥穗、鋼絲等意想不到的材料。美術館的展出選擇上更傾向于多元、多樣化,向市民提供不同類型、新鮮視野、不同文化元素的作品。”吳建軍介紹道。
目前在國際上,水墨已經漸漸上升為一個大水墨的概念。水墨材質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藝術家們不僅僅試圖用攝影、版畫、錄像及雕塑等創作類型,還有不少大型裝置、觀念行為、電子山水、建筑影像等表現形式。中國的水墨品質和水墨文化開始有各種新型語言介入。
吳建軍認為,對于一個畫家而言,可以有自己的趣味和堅持,但對于一個美術館館長而言,傳達中西對話、堅持文化自信、引領美術館是一種責任和擔當。
從較早蘇軾等人提出的“士夫畫”到錢選等所謂的“戾家畫”,再到明末董其昌拋出南北宗論倡導的“文人畫”,直至五十年代“新國畫”、“彩墨畫”,八十年代“實驗水墨”、“水墨畫”乃至當下所謂的“新水墨”等稱謂。水墨一直在變化,水墨延續至今沒有變的是什么?
“是延續千年的中國文脈和精神價值。文化大多數是無用之用,它唯一的作用是在任何喧囂的時代給人們的內心留一個白,留一塊寧靜。你問我水墨文化和美術館在消費時代究竟還有什么功用?如同畫家用水墨造境,美術館給城市的內心造境,留一片可暢想之地。”道別之際,吳建軍特別向記者提及建立中小學、藝術院校教學成果試驗創作基地和藝術沙龍活動的開展情況。
編輯:soul
責任編輯:崔翠 許小仙